瓷器在黄昏里学会弯曲,
光,最温驯的囚徒,
顺着圆弧的刑具流淌。
某个不被提及的纬度,
我们曾共用过一片
游移的静。
总在阖眼的刹那,
暗处浮起未竟的形貌——
半盏凉透的茶,
在木质纹理间迂回成
虚构的河。
某只抽屉深处,
丝绸包裹的晨露,
蒸发成通往旧日的
秘径。
站台的风总在子时折返,
搬运着月光的碎银。
而钟摆左侧,
一小块缺席持续生长,
柔软,坚定,
充满棉絮的耐心。
我们练习悬置——
把地名晒成书签,
将气候收进火柴盒。
当对话渐次剥落成蝉蜕,
寂静的内壁,
便开始生长天鹅绒。
如同某局未竟的棋,
黑与白相互让渡疆域,
在格子的深渊里,
完成一场缓慢的
光合作用。
总会有的:
当季风转向时,
某扇窗自动溶解;
某段楼梯在黑暗中
延伸出新的谅解。
而所有等待的形状,
终将汇聚成
一枚透明的锚,
泊在自身的
完整性里。
无需日历的赦免,
时间在此处打盹,
毛边呼吸起伏。
我们成为各自
最妥帖的遗址,
在光的考古学里,
保持恰好的
风化。
最终我们以缺席圆满在场,
像信纸上未盖的邮戳,
拥有最远的抵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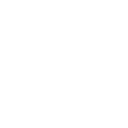 赞(14)
赞(14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