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华三叠
由 傲雪寒梅 · 李夫人 发表于 2025-12-20
冬日的紫禁城,是一座被雪擦亮的记忆。
雪落下来时,最先失语的是那些脊兽。獬豸的角,狎鱼的鳞,斗牛的身躯,渐渐被温柔的白色重新勾勒,显出一种罕见的、近乎温驯的沉默。朱红的宫墙在雪的映衬下,红得更深,更沉,像是凝结了的血,又像是封存了的火。金色的琉璃瓦歇山顶,此刻都覆上了松软的雪被,只有檐角倔强地探出些璀璨的边,提醒着这里曾有过的、照耀四海的荣光。
太和殿前的广场空无一人。雪掩盖了所有足迹,仿佛千百年来,从未有人在此跪拜,也从未有仪仗在此行进。风贴着汉白玉的蟠龙御道低低掠过,卷起细雪,发出一种类似古埙的、幽微的呜咽。那声音空旷而寂寥,钻进耳朵,直落到心底去,将心也拂拭成一片白茫茫的干净。站在这里,你会觉得时间并非流逝,而是就这样一层一层,如同雪片般,静静地、缓缓地沉积下来。繁华与倾颓,煊赫与落寞,都被这无边无垠的素白平等地覆盖、安抚,最终沉淀为一种超越悲喜的、巨大的宁静。这雪,仿佛不是从天而降,而是从这宫阙六百年的深呼吸中,凝结出的、一片清冽的虚无。
当这雪的清寂在记忆里尚未化尽,意象便陡然转入一片丰沛的、几乎要流淌出来的浓绿与嫣红之中——那是颐和园的盛夏。
热浪是看得见的,在万寿山的林木间微微颤动。但一临近昆明湖,那股子燥气便被浩渺的水光吸去了大半。这里的绿是分层次的:近岸垂柳是嫩而娇的翠色,仿佛能掐出水来;远处山峦是沉甸甸的墨绿,叠嶂含烟;最妙是湖中荷叶的绿,田田地铺开去,肥硕,油亮,在烈日下泛着一层蜡质的光泽,那绿是饱含生命力的,几乎有些跋扈了。而在这无边的绿意之上,是星星点点、或粉或白的荷。有的开得正好,花瓣舒展,坦然地承受着天光;有的犹抱琵琶,在阔大的荷叶庇护下,露出一角娇羞。
而这一切生动的铺垫,似乎都是为了黄昏时,献给那座桥的盛大典礼。十七孔桥,在白日里只是一道优美的白色弧线,连接着岸与岛。唯有当夕阳西垂至一个恰好的角度,它才骤然显露神迹。金红的光芒,不再是漫洒的,而是凝聚成一支支光的箭矢,精准地、充盈地穿过每一个桥洞。那一瞬,冰冷的石桥仿佛被注入了滚烫的熔岩,十七个圆拱化作十七只金色的眼睛,沉静地凝视着即将消逝的太阳。光芒在粼粼水波上拉出长长的、颤动的金轨,直抵游人的脚下,仿佛踏着这光轨便能步入那辉煌的源头。佛香阁、西山、乃至整个喧嚣的尘世,在这桥孔吞吐的天地玄黄中,都沉寂下来,成了这片刻永恒的陪衬。这辉煌是慷慨的,也是吝啬的,它只持续短短一炷香的时间,便随着日轮的彻底沉没而骤然收回,空余一座渐渐冷却的、重归沉默的石桥,与满湖怅惘的紫灰色波光。这夏日的欢愉,因而有了一丝悲剧的诗意。
而这“欢愉”与“诗意”的尽头,必然需要一场更根本的清醒。这清醒,藏在秋日天坛那片亘古的蔚蓝之下。
步入圜丘,首先感到的是一种“空”。不是缺少物件的空,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、充满仪式感的“留白”。脚下是巨大的圆形坛面,一层层向上收束,除了规整的栏板与螭首,再无任何赘余。人们的视线无处停留,只能不由自主地向上,向上,投向那毫无遮拦的、秋日特有的高天。那天空蓝得如此纯粹,如此深邃,像一块巨大的、冷冽的琉璃,笼罩着四野。几缕云丝淡得如同未曾落笔的痕迹。
风在这里,声音与别处不同。它在柏树林中穿行时,是沉郁的松涛;掠过祈年殿宝蓝色的圆顶时,是清脆的铎铃;而当它在这空旷的圜丘上自由来去时,却仿佛失去了形迹,只剩下一种巨大的、无声的流动,带着干爽的、近乎凛冽的气息,穿透你的衣衫,涤荡你的肺腑。站在这圆坛的中心,人便成了天地间一个微小的、孤立的点。帝王的冠冕,万民的祈愿,王朝的兴衰,在此刻都显得轻飘而遥远。唯有头顶的苍穹,与脚下这象征“天圆”的石坛,以一种极简的、近乎数学的理性之美,昭示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秩序。这里的夕阳,没有孔洞可以穿越,没有波澜可以辉映,它只是均匀地、淡漠地,将整个苍穹染成由金渐紫的渐变,然后将这无边的帷幕,轻轻拉拢。这秋日的天坛,洗去了故宫雪里的历史烟云,滤尽了颐和园桥上那刻意追寻的、易逝的辉煌,只留下人与宇宙之间,最原始、最肃穆、也最直接的对望。那曾穿过十七孔桥的同一缕金辉,在这里,终于摆脱了形式的束缚,回归了光芒本身那无边无际的、沉思的本质。
三处景致,三种时令,三层意境。雪中的故宫,是历史沉淀后的静默与安详,是“止”;夏日的颐和园,是生命与欲望酣畅淋漓的绽放与对至美光阴的捕捉,是“动”,那桥孔吞日的奇观,便是这“动”最辉煌的顶点与挽歌;而秋光里的天坛,则是超脱了具体历史与感官欢愉,指向抽象与永恒的“思”。它们仿佛一部恢弘乐章的三个乐章:慢板、辉煌的快板与庄严的广板。而傍晚那缕金辉,便是穿梭其间的同一主题旋律——在故宫,它是沉静的余韵;在颐和园,它是奏鸣的高潮;在天坛,它是归于宇宙和谐的尾音。当你依次走过,仿佛也经历了一个文明的精神历程:从奠基的沉重,到盛期的绚烂与焦虑,最终归于对永恒秩序的深沉叩问。那贯穿其间的、复杂而高贵的一脉气韵,也就在这雪之洁、桥之辉、天之旷的流转与呼应中,得以完整,得以成全,亘古如新地,在这座古都的脉搏里,沉着地跳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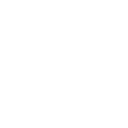 赞(10)
赞(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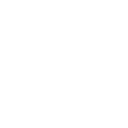 赞(10)
赞(1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