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云阶与琉璃雪界》
由 傲雪寒梅 · 李夫人 发表于 2025-12-13
踏过最后一道山门,喧哗便如退潮般遗在了身后。沿着石阶上行,一级,复一级。起初还有蝉声在耳边作细碎的牵引,愈往上,连这声响也稀薄了,消散了。石阶被千万遍的步履打磨得温润,泛着青灰色的光,边缘处被苔藓悄然侵染,茸茸的一线碧色,像是光阴本身在此打了个盹儿,留下的梦的痕迹。
路是渐渐陡起来的,两侧的密林也换了神色。那绿不再是山脚下那般奔放泼辣的油绿,而转为一种沉甸甸的苍碧。古树的枝干虬结着,探向虚空,叶片却细密如针,重重叠叠,滤下的天光便成了碎汞,斑斑驳驳地洒在阶上,也洒在行人的肩头,清沁沁的,带着一股子草木的凉意。这时节,雾便不期然地来了。它并非弥漫天地的那种大雾,而是丝丝缕缕的,从深谷里,从岩隙间,袅袅地蒸腾起来,行走其间,人也仿佛失了重量,成了这流动的乳白里一个恍惚的影子。周遭的一切都模糊了轮廓,声音被吸得干干净净,唯有自己的呼吸和心跳,在耳鼓上沉沉地擂着,竟成了这无边寂静里唯一的注解。
及至半山,转过一道近乎垂直的“之”字弯,眼前豁然一朗。雾忽然退开了些,像舞台的幕布向两边徐徐拉开。只见无数石峰,陡然从脚下深不可测的渊壑中拔地而起,一柱柱,一簇簇,赤裸着铁灰色的身躯,瘦削、峻峭、沉默。它们并非井然有序地排列,而是恣意地、嶙峋地攒聚着,仿佛远古某场惊天动地的崩塌后,时间骤然凝固,留下了这一片石的森林。这便是那“十里画屏”的骨骼了。奇的是,几乎每座峰巅,都驮着一小片亭亭的绿,像是这沉默的巨人为自己戴上的、仅有的、孤独的冠冕。人立在此处,看脚下云涛翻涌,石峰在云海中浮沉,时而清晰如咫尺,时而隐没如幻影,方才觉得自己渺小如芥子,而这山,这石,这永恒的缄默,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。
而这一切的嶙峋与缄默,都将在另一种时节里,被重新书写。
那是雪后。雪是子夜开始落的,待到晨光初透时,整座“十里画屏”全然换了笔法。往日铁灰色的石峰,此刻都裹了雪,线条变得圆融而柔和。一座连着一座,延展开去,果真成了天地间一架巨大的、素白的屏风。但这屏风上的画,并非工笔,而是写意;并非彩绘,而是水墨。浓处是山脊背阴面堆积的深雪,淡处是岩壁上勉强露出的些微黛色。云雾还未散尽,丝丝缕缕地缠绕在峰腰,更添了几分渺茫与虚幻。雪还在落,不大,是那种慵懒的、打着旋儿的飘洒,将远山的轮廓晕染得愈发朦胧。静,静得能听见雪片叠在雪片上的、那几乎不存在的微响。这绵延的屏风,便在这万籁的寂静里,舒展着它清冷的、亘古的梦境。
复行数百步,抵达山巅那废址古观时,景象又为之一变。尤其是在雪霁之后,那一点金顶,会在无边的素白与青灰中,蓦地跳了出来。白雪覆满了重檐,却盖不住那琉璃的璀璨。尤其那最高的殿顶,积雪沿着瓦垄的弧度,堆积出饱满而温柔的曲线,但瓦当、檐角,以及屋脊上那些镇兽的轮廓,依然清晰。雪是白的,是那种吸收了所有天光、纯净到近乎虚无的冷白;琉璃是金的,是历经香火与岁月、沉淀下来的、温润而沉着的暖金。这两样颜色本是对比,此刻却交融得天衣无缝——金顶因白雪的围镶而愈发庄严夺目,白雪因金光的映照而平添了几分神性的辉晕。
日光渐渐强些时,从云缝里漏下的光柱,一道正好落在金殿的上方。刹那间,那覆雪的琉璃顶活了。不是刺目的闪耀,而是一种从内里透出来的、雍容的流光。每一片瓦都像被点燃了边缘,积雪的凹陷处投下淡蓝的阴影,凸起处则跳跃着细碎的金星。那光仿佛是有重量的、温暖的,在与冰雪清冷的质地做着最柔和的抗衡。看得久了,竟觉得那整座殿宇,连同它承载的古老信仰,都在这冰清玉洁的世界里,微微地、温暖地呼吸着。偶有山风过处,檐角积雪便簌簌地落下一些,扬起一小片晶莹的雾。风铃响了,声音被过滤得清越无比,空空地落在雪谷里,余韵悠长。
这便是老君山的全貌了。有“云阶”的蜿蜒与探寻,有登临绝顶后“虚静”的空茫;更有“画屏”在冰雪点化下的幻境,与那琉璃金顶在素白世界里永不熄灭的温暖光亮。它告诉你,攀登的过程是滤去尘嚣的修行,而最终抵达的,并非一片枯寂的寒冷,而是一种被雪擦拭过的、更为明澈的庄严,一种在极致清静中显现的、笃定的辉煌。
待到日头再偏西一些,金色的光芒转为瑰丽的橙红,无论是晴日的云海,还是雪后的画屏,都浸在了一片暖融融的暮色里。该下山了。回望来路,山已重新被夜色与雾霭拥入怀中,只剩下庞大而沉默的轮廓。但鞋底传来的微痛,肺叶里清冽的气息,心头那一小块被寂静洗刷过的明净,以及眼中那抹白雪映照着琉璃金顶的、永不褪色的光晕,都在确凿地证明:你曾叩访过一片云雾与冰雪深处的永恒。那永恒里,有阶,有屏,有顶,更有行走其间时,那颗被悄然拂拭过的人间之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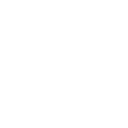 赞(12)
赞(1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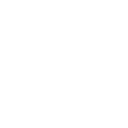 赞(12)
赞(12)